心理科普
团体治疗文献||作为自体与团体互动肖像的梦境日期:2025-12-20 浏览:583

译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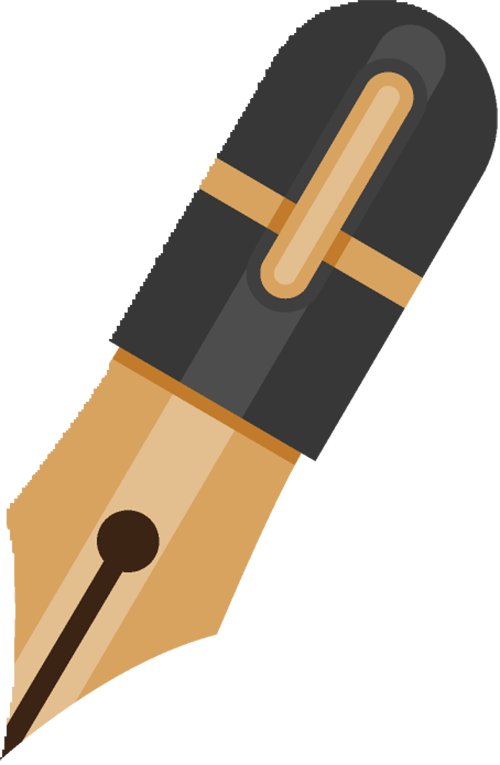
本文从自体心理学视角,重新诠释了团体治疗中梦境的意义,指出梦境是“个体与团体互动关系”的肖像,既反映个体未被满足的自体客体需求与自体状态,也映射出团体整体的情感氛围与动力过程。文章强调,治疗工作的关键不在于“解析”梦境,而在于识别其中蕴含的成长方向与修复契机,借助团体的共鸣与反思,将梦境转化为促进个体发展与团体凝聚力的催化剂。
对于临床工作者而言,本文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操作框架。其核心在于引导团体关注梦境中代表新生希望的“前缘”内容,通过共情性探索,将团体转化为一个安全、回应性的“自体客体”,从而帮助成员获得新的关系体验,打破旧有的创伤性重复模式。文中的两个临床案例生动阐释了这一过程如何在实际治疗中促成改变。

作者:Walter N. Stone & Sigmund Karterud
原文来自Walter N. Stone主编Contributions of Self Psychology to Group Psychotherapy:Selected Papers,2009年,55-66页。
本文利用AI翻译整理,仅用于学习交流,版权属原作者所有。尊重译者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团体心理治疗中呈现的梦境,描绘了个体与团体之间辩证关系的不同侧面。自体心理学视角着重强调团体整体当前的自体状态与个体自体客体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焦点,治疗师应协助团体深化其觉察力与反思能力,以识别梦境意象所传递的、正在显现的新能力(“前缘”),以及实现这些能力所需的人际回应。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个体与团体打破并转化强迫性重复的链条。我们将通过两个临床案例对此方法进行说明。
作为自体与团体互动肖像的梦境
自弗洛伊德发表其经典专著(1953/1900)以来,梦境一直被视为通往潜意识世界中愿望、冲突与防御的途径。传统上,在患者自由联想的辅助下,释梦的任务在于解读梦境所伪装的那些潜意识元素。与此不同,自体心理学则将关注点集中于梦境对自体的呈现,以及自体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关乎过去,也关乎此时此地。正如奥恩斯坦(1987)所言:“梦总是关乎自体;也就是说,梦总是将自体体验的各个方面呈现给做梦者。”(第101页)
阿特伍德与斯托罗洛(1984)强调了将梦境概念化为具体象征的价值,这些象征“旨在实现特定的体验组织,其中特定的自体与客体构型……被戏剧化地呈现并得到确认”(第103页)。他们指出:“通过生动地具象化自体受威胁的体验,梦境象征将自体的状态带入焦点意识,并伴随着唯有感官知觉方能赋予的确信感与现实感”(第104-105页)。福沙格进一步强调了梦境意象对自体的整合与综合功能,他提出:“梦境的首要功能在于心理过程……与[心理]组织的发展、维持(调节)及必要时的修复”(1997年,第433页)。他强调,情感调节在维持或修复受创自体方面是梦境的一项核心功能。
在个体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随着治疗进程深入,梦境会逐渐浸润移情关系的色彩。而在团体心理治疗中,梦境则成为对团体这一高度复杂社会情境的反应——做梦者自身正是该情境的组成部分。临床文献中补充了“团体梦”的概念,特指那些显性内容中包含对团体的具体或“轻度”伪装指涉的梦境(卡特鲁德,1992)。我们认为,在心理治疗团体中报告的大多数梦境,实际上呈现了团体与个体自体之间辩证互动的不同侧面。
自我心理学视角下的团体梦境
从自我心理学的视角审视梦境,其可能表达个体的表现欲/夸大性渴望,或对自体客体确认的寻求(Stone & Whitman, 1977),亦或是与理想化自体客体融合的愿望(Stone, 1992)。在团体中报告的梦境,可能反映了对特定成员回应的期待,或是做梦者对团体整体之内在体验的表征(Harwood, 1998)。团体梦境也可能反映出对参与团体的抗拒;这种抗拒或许代表了过去创伤性的家庭或团体经历,或是那些未能提供必要"最佳反应"的经历(Bacal, 1985)。团体梦境还能描绘团体的解体或瓦解,表现为物体的破碎,这可能是由实际或预期的丧失(如成员退出、团体活动规律中断)所激发,或是源于对早期丧失(如死亡、离异)的再度唤醒。
在团体中,对自体的威胁可能源自多个方面。违反团体规范或界限的行为,例如团体外的私下联络或长期迟到,可能在意识层面或仅在阈下意识中被体验,并在梦中以断裂的篱笆或坍塌的墙壁等象征形式反映出来。情感上的过度刺激,如强烈的情欲吸引、原始的嫉妒或被理想化,可能催生出洪水或龙卷风等梦境意象。在较不剧烈的层面上,那些看似无害的互动——如接受建议、提出一个刚刚被回答过的问题、重复他人的评论——也可能引发自恋性损伤,被个体体验为对自体的伤害性(创伤性)冲击,并影响其内心的团体意象。这类互动常见于团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其特点常伴随接受者未言说的羞耻体验,这可能摧毁他/她对团体的信任。一个梦境可能就是患者对这种破坏性体验的传达。
我们先前曾提出,理解团体整体现象有三种相关视角,这些视角可能在梦中得到反映:1) 团体作为客体,例如被象征为"坏母亲",具体可表现为危险的或不可接近的个体,或一座空建筑;2) 团体作为自体客体,为自体提供支持性功能,例如表现为一个家庭正在享用盛宴;3) 团体-自体。这些视角并非互斥。恰恰相反,它们彼此丰富,我们将在临床案例中尝试加以阐明。
团体-自体这一视角最初由科胡特(1976)提出,指的是所有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协作的、超越个体层面的集体性规划。也就是说,个体会将团体的价值观、目的、希望、理想和目标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心理治疗团体的规划,正是通过成员与有限数量的同伴及治疗师之间的深入互动,来促进自我理解与自我发展。团体-自体承载着自由开放的交流、对对话的信任、相互尊重与关怀、公平感以及作为支持性共同体一员等理想(Karterud & Stone, 2003)。我们认为,这些理想根植于一种进化意义上的关切,即将自我视为与团体交织共存的一部分。然而,这些理想不断受到退缩、猜疑、敌意、贪婪、嫉妒、竞争、憎恨及报复欲的侵蚀。试图在个体层面及团体-自体层面解决这些冲突,构成了治疗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主题。
因此,如上所述,对自体的伤害也可理解为对团体-自体的损害。例如,一位重要团体成员的退出,很可能在多个层面产生意义,包括在团体层面造成的丧失感,并由此导致团体-自体因感觉失去了该成员对团体工作的贡献而受损。在探索反映自体耗竭或碎裂的梦境时,若不考虑它们也可能代表团体-自体状态转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探索将是不完整的。

治疗考量
从自体心理学视角出发的临床工作者认为,探讨梦境的目的在于帮助成员理解其自体状态的波动、他们对人际回应的需求,以及新的存在方式可能浮现的契机。这包括自体保护、自体修复与自体提升的过程。利文斯顿(2001)指出,在团体中呈现的梦境无法以经典意义进行完全分析。“在团体中处理梦境的价值,不在于获得完整解析和有序处理的机会。其清晰的价值在于能够激活并深化团体进程”(第24页)。除了表征个体的自体或团体-自体阶段外,梦境还可能以隐喻方式描绘治疗过程的某些方面。连续的梦境场景可以像一系列画面般,呈现成员自体或对团体互动的感知的多个侧面。
自体心理学的病理学模型是发展性阻滞,而非内心冲突(科胡特,1984)。患者不仅为掌控旧冲突而重复其发展性困境,同时也尝试着发展性的推进。托尔平(2002)将这些“呈现”标记为“后缘”与“前缘”。她用“柔嫩卷须”这一表述来描绘前缘的试探性特质,意指发展性努力的脆弱与谨慎。无论是这些代表新发展可能的“前缘”元素,还是反映旧有行为或情绪模式重复的“后缘”元素,都可能嵌入在任何交流中,尤其是梦境里。
利文斯顿(2001)报告了一个梦例来阐释此方法:梦中,一位做梦者被一只“很恶心”的大蟑螂吓到,却无法杀死它。他说尽管那只虫子的头“开始看起来像小猫的头……我还是想醒过来逃离那里,因为那虫子死不掉”(第21页)。在探讨了梦中一些可怕、丑陋和令人恶心的部分后,另一位成员注意到了小猫头的出现。这一介入将讨论从做梦者自体那重复出现的糟糕、丑陋方面,转向了其所代表的更温柔、美好的一面——即“前缘”。在对小猫头浮现进行反思后,团体聚焦于做梦者身上正在发生的转变,并识别出了其他个人的转变。紧接着这段材料,一位女性报告了一个让她感到羞耻的性梦,这使她得以谈论自己先前未曾探索且令人恐惧的面向。
对积极(前缘)变化的识别,可能被误解为一种逃避,即回避进一步审视破坏性和丑陋的自我感知。然而,在此例中,结果却是另一位成员能够报告一个梦境,将她自我中先前未探索且令人恐惧的层面带到了前台。这一顺序表明,聚焦于前缘可以起到镜映自体客体的功能,能增强治疗联盟,从而促进患者或团体成员对更深层、后缘的自体议题进行探索。从团体-自体的视角看,对前缘的关注强化了团体“欣赏每位成员潜能”这一理想。
在团体中报告梦境的一个优势在于同伴的在场与可参与性。在治疗师的阐释协助下,成员很快能认识到,一个梦境不仅是关于做梦者的个人陈述,还包含着团体文化及团体话语的某些面向。当做梦者无法对其梦境产生有意义的联想时,其他成员可以贡献出自己的联想。这些联想可能指向情绪、主要元素、片段,或是梦境序列中描绘团体内部动力过程的各个方面。如上述案例所示,成员可以学习如何就梦境元素及其呈现的过程进行评论。这种能力对于一个功能良好的分析性团体-自体至关重要。
我们对梦境的处理方式并非刻板固定。我们相信任何被说出的话都会被所有人听到,治疗师的发言尤其如此。因此,任何聚焦于做梦者的梦境干预或探索,都会被在场所有人听见并体验。他人的反应可能包括将治疗师体验为促进性的自体客体,或是一种破坏性、分裂性的力量。将梦境阐释为反映团体整体的过程,几乎必然无法完全准确,并可能对一位或多位成员造成自恋性损伤。通过观察每次干预后的团体进程,治疗师可以深入了解受创个体为稳定自体所作出的反应。福沙格(2002)指出,贯穿生命周期的自体客体回应性能修正先前的自体组织并促进成长。他断言,若缺乏此类体验,个体将固着于童年早期形成的关系模式。同伴与治疗师对梦境的共同探索,为自体客体回应性提供了模板,并丰富了不断演进的团体文化——这种文化珍视情感联结、自我反思,以及理解他人拥有独立心智与视角的能力。
斯特恩等人(1998)强调了促成改变的“关系性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学习既发生在意识层面也发生在无意识层面。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相遇时刻”,它反映了真实、深具共鸣的个人接触。在共同理解梦境的工作中,无论成员之间还是治疗师与成员之间的互动体验,不仅对做梦者,也对所有在场者都可能提供这样的时刻。这些被强烈体验的时刻,很可能提升成员管理情绪的能力,并使他们学会将他人视作拥有主体性的个体而非被原始地用于满足自身需求的客体。
福纳吉等人(2002)强调了另一项可能通过共情性梦境探索来促进的发展任务。这项工作有助于推动从“心理等同模式”(一种将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等同化的思维特征)向"自我反思功能"(一种能理解他人内心愿望与情感的思维模式)的转变。来自治疗师或成员对梦境的共情回应,可能创造“相遇时刻”,从而深化对话。
在以下两个案例中,我们将展示梦境如何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媒介,以及团体内部的工作如何在个体与团体整体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从而促进个体发展(自我反思与表征功能),并化解受阻的团体-自体。
临床案例1——“性侵犯”
吉姆对艾琳的行为被其他几位女性成员理解为略家遮掩的性引诱,她们在数次会谈中表达了对此的不满。男性成员,尤其是惯用疏离作为防御的弗兰克,则抗拒介入其中。正是在此背景下,弗兰克报告了一个梦境:“有个男人和女人性交。接着轮到我了。但我发现她的生殖器发育不良,无法进入。这一切发生在阳台上。这时有人敲门。我猜是有几个男人要来强奸她,就从排水管逃了下去。下到一半我改了主意,又爬回去。阳台上我看到几个男男女女正坐在那儿交谈”。
弗兰克的联想迅速转向他十岁时的一件事。他十五岁的哥哥和几个朋友曾试图诱奸(甚至可能是强奸)他十二岁的妹妹。她勉强逃脱了。当时的他是一个被动、既兴奋又不安的目击者,事后因未能干预而极度自责。讲述时,弗兰克的愤怒不断加剧——主要针对哥哥,也针对自己的懦弱。吉姆那被女性们重点指出的诱惑性行为,让弗兰克想起了哥哥当年的企图。他当时无法介入,正如此刻他也无法干预。团体很快理解了弗兰克的童年经历与他此时此地的愤怒和羞愧之间的联系。
治疗师指出,关于梦境最后的部分还讨论得很少。他提出:“过去与现在存在一个关键差异。童年时期的弗兰克无人可以诉说这段羞耻的经历,但在梦中,他发现了‘几个男男女女正坐在阳台上交谈’。我在想,这是否意味着有机会与团体成员进行交流。”尽管弗兰克害怕与象征意义上的哥哥斗争,也害怕因梦中的性欲受到谴责,但他最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阳台”。那些交谈的成年人所呈现的良性氛围——这种他在童年时期缺失的环境——如今使他能够重新面对这段过去,并获得对自身及团体经历的新视角。
我们认为这个梦是由团体-自体内部的冲突所激发的,这种冲突关乎何种话语规则应占主导。这些规则包括一种“假装模式”——作为发展性的一步,父母或年长的孩子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向孩子展示:现实可以通过行动被扭曲(Fonagy等,2002,第57页)。假装模式与普通社会现实的意义不同,它并非真实的。在分析性团体中,假装模式的话语是必要的,它能建立一种安全感,使成员能够体验并表达那些令人羞愧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假装模式的存在是“被标记”的,即通过某种非言语方式传递信号。
吉姆曾声称自己只是遵循团体规范,说出心中所想而已。他质问:“难道性感受在这个团体里是禁忌吗?”女性成员回应说,问题在于他谈论性感受的方式——那不是反思性的,而是带有虐待和剥削意味。她们感受到他在宣泄自己的欲望,并进一步指责他未能“标记”自己的言语,逾越了团体话语中既定的假装模式(Austin,1962),认为他是为了满足感而展现其原始未经消化的性欲,而非为了反思。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任务并非在这场冲突中选边站队。吉姆对待艾琳的方式中很可能存在“满足自我”的成分,但这些成分无疑被女性成员放大了。当冲突升级时,很快发展到投射性认同的程度,激烈的相互指责占据了主导,反思功能则被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团体-自体暂时被心理等同思维所弥漫,其结果是丧失了平常更具游戏性的对话方式。
福纳吉等人(2002)指出,在有成熟成人引导的情境中进行游戏,有助于将心理等同思维转化为表征性思维。弗兰克回忆起的童年创伤事件,正是一段“游戏假装模式”的边界丧失的插曲。起初只是(带有性意味的)游戏,逐步升级并几近演变成非游戏现实的噩梦。对弗兰克而言,这段插曲具有“模型场景”的特性——特定互动触发了个体或团体内部充满核心情感的反应(Correale & Celli, 1998; Lichtenberg等, 1992)。他形成了性格层面的防御机制,使自己在环境中保持疏离状态。他成为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更深地卷入可能威胁到他涵容或应对情绪反应的能力。他缺乏在能够守护边界的良性成人陪伴下,与危险想法和感受进行“游戏”的经验。团体-自体的动力过程开始与他潜意识中的噩梦相似。看似天真、游戏性的冲动可能转化为具有威胁性的现实。
治疗师在这段工作结束时的诠释具有教育性目的。通过将阳台上交谈的人们等同于团体成员,他让弗兰克和其他成员更清晰地意识到团体的自体客体功能——即在团体中获得安全、回应性场所的体验,这是探索可怕幻想的前提。对弗兰克而言,这个团体与他童年所缺失的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强调“阳台团体”中差异化成员间的交谈与思想交流,治疗师将焦点集中在做梦者对获得新体验的希望上,这本质上就是“前缘”(Tolpin, 2002)。这个整体意象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惊喜感和对归属的渴望。
尽管学界关于“领悟”与“(新)关系体验”孰重孰轻的争论持续存在(Fosshage, 2002),但这个临床案例似乎阐明:新的关系体验(团体的自体客体功能)如何能促进自我理解(领悟)。而新的自我理解反过来对后续治疗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修通自体结构中的病理性情结提供了新的视角。
临床案例2——“游戏团体”
玛丽讲述了以下梦境:“我在一个会议厅里,有人正在严肃地讲话。我旁边坐着艾伦(另一位成员)。我们手挽着手,左右摇晃。我们玩得很开心,笑着。”这个梦很快与玛丽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联系起来。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女性,全身心投入专业和社会事务,却牺牲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对玛丽而言,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如何能过上更快乐的生活。在梦中,艾伦成了通往这一目标的桥梁——他将成为享受乐趣的榜样,从而扩展玛丽受限的自我感,这是一种孪生自体客体移情。团体围绕“自我牺牲”和“渴望玩乐”的主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治疗师觉得没有干预的必要,尽管他注意到团体没有评论这个反抗主题,会谈从严肃的讨论转向游戏和欢笑。在随后的讨论中,艾伦异常活跃和自信。他在玛丽梦中的角色显然让他充满活力。
过了一会儿,治疗师指出了艾伦活跃度的提升,并将其与艾伦在上次会谈中报告的一个梦联系起来。在那个被做过俄狄浦斯式解读的梦里,艾伦拥有一部比治疗师更引人注目的手机。治疗师提出,此前在团体中相当抑制的艾伦,现在似乎触及了自身更自信的一面。对艾伦而言,活跃曾意味着与治疗师进行危险的竞争。但现在情况似乎不同了。治疗师注意到,在之前的梦里艾伦用手机给一位女性打电话,于是他继续展开这个长篇诠释,指出仿佛玛丽理解了艾伦梦中那个无意识的(但已被诠释过的)信息。玛丽自身的俄狄浦斯冲突涉及需要满足父亲对严肃处理重要社会事务的要求,并放弃与同伴进行性探索的游戏。如今敢于在性领域挑战治疗师的艾伦,似乎为玛丽确认了她自身一些被压抑的性和快乐欲望。通过这种确认,她也敢于反抗那个极其严肃的父亲/治疗师形象了。为了佐证诠释的最后一点,治疗师提醒玛丽回忆起几个月前她参加治疗师在一次专业会议上演讲的经历。在这段长篇诠释之后,团体沉浸在对这些梦境主题的进一步联想中。
这些梦发生在一个功能良好、长期运作的分析性团体中。它们源自一个成熟的团体-自体基质,没有受到任何被投射性认同弥漫的冲突阻碍。这个团体-自体的特征是建立了良好的“假装模式”,为成员提供了与“危险事物”游戏的自由。
我们认为,一个成熟的团体-自体至少已整合了关于社会无意识的某些概念,即成员通过无意识机制相互影响并影响团体-自体。虽然无意识的现实性无法被证明,但其效应可以通过可观察的此时此地互动与梦境叙事之间的交织来展现。在此案例中,治疗师清晰地阐述了玛丽和艾伦的俄狄浦斯冲突如何交织、如何涉及治疗师、如何在梦中被描绘以及在团体剧场中上演。治疗师的干预代表了对两位患者“前缘”工作的确认(镜映)。两人都在探索新的、更自信的行为可能性。
讨论
在《不可能的职业》中,珍妮特·马尔科姆(1981)将临床工作者的任务描述为:保持多重观察视角,不过早封闭那些可能富有成效的、用于理解治疗性沟通的路径。哈伍德(2002)列举了七种她可能用以审视梦境的不同视角。团体治疗师在这方面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因为任何梦境都可能在多个层面进行传达。团体心理治疗中呈现的梦境,是梦者试图向自己及团体中他人传达关于自体、他者、自体-他者关系、团体过程和/或更广泛环境(包括更普遍的文化)信息的事件。它可能指涉过去、现在或未来。显性梦境意象不再仅仅被视为被伪装愿望的表征,而可被视作一种隐喻,或梦者当下关切的表征。具有治疗性的并非梦境本身,而是后续那些可能扩展并巩固成员自体或团体自体的回应。我们在前文的案例中已尝试阐明这些观点。
在我们的第一个案例中,弗兰克受到团体互动中蕴含的性张力的激发,呈现了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呈现了他在当前情境中关于被动性与羞耻感的冲突。性无能的直白呈现、他的逃离以及最终回到温和对话发生之处的选择,都传递出他对团体的感知——这个团体具备服务其发展性推进动力的潜能。第二个案例传达了玛丽即使在“严肃事务”背景下,游戏能力亦得到提升的感受。在这两个长期治疗的案例中,团体场景在一个梦中被直接呈现,在另一个梦中则通过特定团体成员被纳入梦境来体现。两者似乎都表明,团体被体验为一个足够安全、能够发生成长与改变的场所。
任何团体梦境的价值当然在于它对梦者及其他成员的双重传达作用。治疗师与其他成员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应,以充分利用此机会,取决于多重因素。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患者呈现梦境,是为了传达那些阻碍其有效利用团体的、团体情境内的困境;而这些梦境也成为了向促进成长方向改变的催化剂。
正在招募的团体(点击下方链接可查看)
周一晚间地面团体:www.boboxinli.com/display.php
周三上午线上+地面团体:www.boboxinli.com/display.php
周五晚间网络团体:www.boboxinli.com/display.php
周日上午网络团体:www.boboxinli.com/display.php
译者简介










